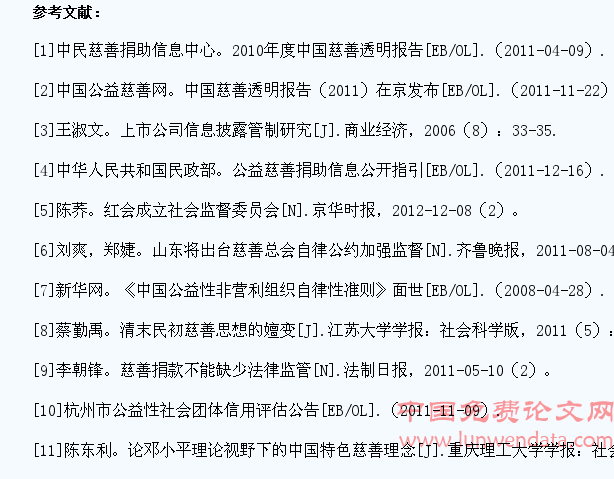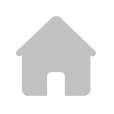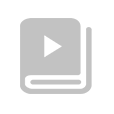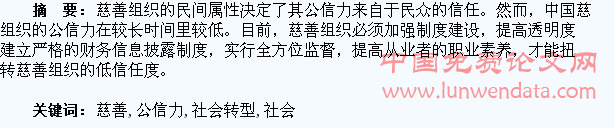
近几年,慈善组织因各种问题被媒体揭秘之事屡见报端,尤其是2011年发生的“郭美美事件”①,将多年来大家对慈善组织的不信赖推向高潮。郭美美事件是一个引燃点,大范围地触发了公众积郁多时的对整个慈善组织的不信赖,使慈善组织陷入紧急的信赖危机。慈善组织要痛定思痛,借用该事件反映出的问题,推进慈善组织管理规范改革。
1、规范信息公开规范,提升信息透明度
透明度是衡量慈善组织公信力高低的主要指标,这是由慈善组织的民间属性所决定的。现在,国内慈善组织透明度情况让人悲观。据民政部下属机构“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慈善透明报告》,抽取样本为99家,通过打造包含4项一级指标、37项二级指标、满分5分制的透明慈善指数,全方位评估慈善组织的信息透明度。评估报告显示,全国只有25%的慈善组织信息透明度较高,其中业务活动信息透明指数为2.43,财务信息透明度则最低,为1.52.各类慈善组织中,基金会信息披露相对较好。在社会公众互联网随机调查中发现,同意调查的近九成公众表示对慈善信息公开不认可[1].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2011年使用百分制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进行评估,其设计的“慈善透明指数”体系由以下内容构成:完整性(59个指标,满分70分)、准时性(5个指标,满分10分)、准确性(3个指标,满分10分)、易得性(4个指标,满分10分),共包括71个指标,总分为100分。依据上述透明指标体系,抽取1000家公益慈善组织样本,平均透明指数得分仅33分。其中,年度透明指数在80分以上的组织只有6个,仅占1000家评测样本的0.6%[2],透明度整体得分偏低。这可以反映出国内慈善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和进步水平。调查还显示,只有8%的公众对慈善组织透明度表示认可。这一方面反映了2011年慈善组织持续的问责风暴对公众的影响,其次说明社会公众权利意识、问责意识提升较快,微博等新媒体技术使信息获得方法改变较大,而慈善组织的透明建设速度已大大落后。
透明度是慈善组织存活进步的一项根本法则,事关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和慈善事业的整体效率。提升透明度的核心方法是慈善信息公开。关于信息公开的重要程度,美国大法官路易斯·布兰蒂斯早在1914年就指出:“(信息)披露才能矫正社会及产业上的弊病,由于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灯光是效果最好的警察。”莫茨哈若夫也指出:“信息披露本身就是限制舞弊和差错,如此做的理论依据是公众有知情权,需要通过立法来预防盘剥行为。”[3]如此的至理名言流传百年而依旧具备生命力,由于它揭示了透明度的本质。然而,国内慈善组织信息披露状况非常不乐观,依据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发布的2010年和2011年报告显示,将近一半慈善组织未拟定慈善信息披露方法,没信息披露方法的小规模草根慈善组织数目更多。
慈善事业在中国兴起已有30年,为何还会存在这种局面呢?剖析起来大致有以下几方面缘由:一是整个中国在转型期的规范平台建设跟不上社会变革的速度,譬如慈善行业缺少统一的信息公开标准和公共信息公开平台。二是慈善组织缺少信息披露所需的人力和物力投入。信息披露需要专门的资金和职员,并将它作为事业进步的一部分,但日常不少慈善组织总是看重募捐而不看重将募捐信息、财务信息、发放信息等准时向社会通报和披露。三是慈善组织极少对信息披露的成效进行评估,较少征询公众是不是知道信息披露内容、是不是了解信息披露途径、披露内容是不是是公众想知道的,仅简单地披露财务数据,公众看得枯燥,也不明就里,如此的披露起不到预期成效。四是缺少信息披露的动力,从政府到社会、从规范到法律都对信息披露采取宽容态度,使得大部分慈善组织缺少信息披露重压和积极性。慈善组织生命力扎根于公众的信赖和支持,当公众质疑慈善组织遮蔽信息的时候,慈善组织需要尽快结束这种与公众知情权的博弈,让组织在阳光下运行,让公众知情权得到最大限度发挥,让慈善真正成为“透明的玻璃口袋”,不然,慈善组织将失去公众的信赖,来自公众的捐赠势必降低,最后风险整个慈善事业进步。
为此,慈善组织需要下大力气解决慈善信息公开问题。慈善信息公开是一个从遵循落实强制公开标准到越来越全方位公开的过程,即从强制性公开到自觉地全方位公开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公众的关注力度有关的,在当今信息化年代,大家获得信息的能力、方法和渠道已相当多样便捷,网络使公民获得信息的本钱大大减少,所获得信息的丰裕度和即时度有了较大提升。这就需要慈善组织尽快实行全方位信息公开,以适应信息化年代需要。现在,慈善信息公开至少在三个层阶上需要加快拟定规范化需要:一是在政策环境上,国家要加快健全信息公开规范及有关法律,统一慈善信息公开标准,做到慈善信息公开有法可依,违法必究,这是提升慈善透明度的规范保障;二是在行业规范建设上,国家应拟定推行慈善组织透明度指标体系,打造全国慈善信息报送规范,塑造慈善行业的公共信息平台,健全信息披露监管体系;三是在组织进步上,国家应加大对慈善组织信息披露能力的培训,打造慈善信息披露评估与奖励机制。
现在,国家在规范层面上有《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关于规范基金会行为的若干规定》等法律规范,但对于慈善组织信息公开没专门详细可操作的规范性规定。郭美美事件发生后,民政部在社会重压下,于2011年12月公布了《公益慈善捐助信息公开引导》(以下简称《引导》),使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有了明确参考。《引导》对慈善公开的环节和内容作了较详细规定:
(1)信息公开主体基本信息,包含:机构基本状况(机构名字、成立时间、机构宗旨和业务范围、办公地址、工作电话等)、年检状况、评估结果、处置投诉的联系人及联系方法等。
(2)募捐活动信息,包含:活动名字、活动地域、活动起止时间、捐赠人权利义务、募集款物计划及活动目的、募集款物的作用、募集款物的用法计划、募捐活动的合伙人、募捐活动的方法(义演、义卖或是其他)、募捐款物数额、募捐工作本钱及开支状况等。
(3)同意捐赠信息,包含:同意捐赠款物时间、捐赠来源、同意捐赠款物性质(定向捐赠或非定向捐赠)、同意捐赠款物内容(捐赠种类、捐赠数额),与是不是开具捐赠收据等。
(4)捐赠款物用信息,包含:受益对象、受益区域、捐赠款物拨付和用的时间和数额、捐赠活动和项目本钱、捐助成效(图片、数字、文字说明)等。在捐赠款物用过程中计划有调整的,要准时公布调整后的计划。[论文网 LunWenData.Com]
(5)同意捐赠机构财务信息,包含:年度财务会计报告(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会计报表附注、财务状况说明书)、审计结果报告等。
(6)平时动态信息,包含参与公益投资状况、内部招投标和物资采购状况、主要员工变动状况、项目动态状况等[4].
《引导》需要将组织的主体、募捐活动、同意捐赠、捐赠款物用、同意捐赠机构财务及必要的平时动态等信息公开,并需要接收平时捐赠后的公开时限为15个工作日,重大事件募捐信息,应在72小时内公开,从而使慈善组织有了可操作实行的量化规定,降低文牍主义弊病。《引导》的公布会促进整个慈善行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和行业透明度增强。然而,《引导》只不过一个软性的指导性文件,民政部要在此基础上尽快拟定管理方法,从立法的角度,对慈善捐助信息公开进行刚性规范和实行,尽快使慈善组织强制性地在阳光下运行。
对于慈善信息公开,慈善组织要将它作为策略组成部分,拟定具体手段来实行。第一,慈善组织领导层需要充分看重信息公开工作,这是达成慈善组织进步的势必需要。第二,慈善组织要通过多条渠道解决信息公开问题。慈善信息公开渠道的广泛性是与慈善组织公信力联系在一块的,这就需要慈善组织广开思路,借助行业平台、新式媒体及募捐的资金,投入到信息公开中,将慈善信息公开所需资金纳入到年度预算中,专款专用。第三,慈善信息公开需要打造新闻发言人规范,设立信息专员。慈善信息公开需要专业性人才,慈善组织每年管理着几百万、几千万捐款,假如没现代的记录体系和管理程序,要搞了解每笔款的流向是非常难的。所以,慈善组织需要IT人才,打造综合信息管理软件,实行更细致、更严格的内部管理和更明确、更透明的外部公开。第四,慈善组织应加大信息化管理规范建设,要打造规范档案,打造慈善信息年报规范和慈善信息报送规范。
总之,慈善组织要从信息公开入手,根据《引导》和将来将颁布的信息公开管理方法的规定和需要,尽快着手打造全方位的慈善信息公开规范,迎接透明年代的到来。只有如此,慈善组织才能重新取得公众的信赖,获得社会公信力。
2、健全监督机制,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
没监督的权力容易产生腐败。同样的,服务于公众的慈善组织的权力源于公众的信托,公众信托的权力假如得不到监督,同样也会产生问题,早在2001年,被誉为“中国妈妈”、“丽江母亲”的胡曼莉就是没得到准时的跟踪监督而挪用善款,引起较大社会争议。在近期十年里,慈善监督依旧问题不少,为此,社会各界需要对慈善监督有充分认识,探索慈善监督多样性,越来越形成外部监督和内部监督相结合的立体化监督模式。
第一,应完善政府监督机制。慈善组织与政府不是隶属关系,更不是对立关系,论文格式而是相互合作和支持关系。慈善组织有一部分款项来自政府购买服务,因此,政府无论从社会管理角度还是资金监管角度,都有责任履行好监管职能。现在,政府对慈善捐赠监管主要通过两种方法来运作:一是从法律规范层面对慈善组织进行规范和约束,也可以称之为法律监督。国内先后颁布推行了很多法律、法规与部门规章,如《中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方法》和《基金会管理条例》等,但这类法规与地方性法规缺少统一性和一致性,不只增加了社会管理本钱,也加重了慈善组织的负担。政府需要加快拟定慈善信息公开管理方法之类的行政法规,对于不按规定实行慈善信息公开的组织要在媒体上揭秘,督促其改正;对于违反法律规定的慈善组织要坚决给予处分,过失紧急的应撤销登记。同时,政府要健全执法程序,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水平,在执法层面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建设装修网。二是从实践层面对慈善捐赠资金、年度审察、注册等方面进行刚性管理。政府应在审核慈善机构的预算和决算时明确奖惩规范,做得好的慈善组织可以得到更多的政策打折,政府要从这类信誉好的慈善组织中购买服务。政府要进行跟踪管理,对于违反规定、挪用善款的慈善组织则要严厉处罚,从而起到监督和规范慈善组织运作有哪些用途。
第二,应丰富社会监督机制。社会监督由媒体、民间评估机构及公民个人三位一体监督形式组成,主要负责对慈善组织的捐赠款物用、资助项目等进行监督。具体做法可以是慈善组织聘请职员打造社会监督委员会。现在,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江苏红十字会、青岛慈善总会等很多慈善机构都成立了社会监督委员会。
2012年底,中国红十字会设立的社会监督委员会主要邀请具备深厚专业背景、广泛社会干扰、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和志愿者代表担任监督委员。江苏红十字会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是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并确定的,共收到70份报名表,最后确定21人拟任社会监督委员会成员,未能入选的报名者,将纳入数据库管理,便于以后的“问计”[5].社会监督委员会的设立表明慈善组织开始看重监督用途,但要使监督员真正承担起监督用途,需要健全推行监督的操作程序,使监督员可以随时随地实行监督,而不可以到年底进行突击监督检查,更不可以将监督委员会当摆设。
当今中国,媒体在监督慈善组织和慈善事业进步方面发挥有哪些用途日益增强,尤其是网络的高速发展和2009年以来的微博上线,致使普通民众都可以很容易地将耳闻目睹的事件放在网络晾晒,供数亿网民评说。这种无所不在却又并困难辨识的“监视”成为现代社会的一大特点。
这种监督的功用不可以忽略,近几年在慈善范围出现的多起有损慈善声誉的事件都是由互联网媒体揭秘而引起社会关注的。伴随中国民主规范的健全,媒体在慈善监督方面有哪些用途将日益增强,公众监督方法愈加多样,监督主动性将愈加明显,监督的广度和深度将与时俱增。
第三,应健全慈善组织内部监督机制。慈善组织内部应设立专门的监事会,负责对慈善组织资金的募集、管理、用、增值等活动进行全方位的监督。中国慈善事业经过30多年进步,慈善组织已经认识到自律对于行业进步的重要程度,山东慈善总会会长谢玉堂说,行业自律是达成慈善事业健康进步的头等大事,它关系到整个慈善行业的生死存亡,加大行业自律是慈善事业进步的势必需要,是年代进步的客观需要[6].慈善行业组织已经开始自觉地探索行业间一同遵守的自律规制。
2006年1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进步基金会、爱德基金会三家机构一同发起了“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行动”,并委托NPO信息咨询中心作为自律网盟的实行机构。
2008年4月,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青少年进步基金会、爱德基金会、南都公益基金会、NPO信息咨询中心、上海浦东非营利组织进步中心、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自然之友、地球村、农家女等一批著名非营利组织参与制定的首部《中国公益性非营利组织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发布。《准则》共80多个条约。内容包含:使命、利益冲突、内部治理、集资、财务、项目、职员、非营利组织间的协作关系、信息公开等九个方面[7].《准则》是慈善组织走向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进步的标志,将对加入自律行动的慈善组织提升公信力产生积极影响,也将为其他慈善组织产生示范用途。
总之,政府及整个社会需要履行好对慈善组织的监督责任,使慈善组织真正在阳光下运作;慈善组织本身应尽快打造起有效的融组织自律、行业互律与多元他律“三位一体”的监督机制,促进组织健康进步。
3、提高从业者专业水平和职业素养,推行信用评估规范
慈善从业者的专业水平和职业操守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提高的内在保障[8].慈善组织经过30年进步,其功能从过去扶贫济弱的救助型功能转变为培训开发的服务型功能,慈善功能的转变需要从业者在能力层次上有所提高,慈善组织需要尽快塑造一支有思想、懂业务、会管理、具备较强革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队伍。为此,慈善组织要努力做到从慈善公益项目设计到实行都有专业化的职员来推进,有懂慈善的、有知道市场的、会管理的、懂财务的,也要有懂宣传的,要尽快打造职业化的人才队伍来推进慈善事业进步。其次,慈善事业有其特殊性,其管理的款物来自公众的捐赠,它一手牵着充满善心的公众,一手牵着需要救助的人群,所以,慈善工作者相对于别的人背负着更大的道德风险,慈善从业职员要拥有志愿、奉献、博爱精神,要有一种热情,做到廉洁自律、洁身自爱,自觉抵制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才能适应慈善工作,才会彰显出慈善组织的道德优势,感召更多的人投身到慈善工作中。因此,从事慈善事业的复合型人才,第一应是热爱慈善公益事业,有爱心、奉献精神和责任感的人。所以慈善人才的选拔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要把对慈善事业忠诚又具备专业能力的人选拔到慈善队伍中来,他们出色的工作将是慈善组织公信力提高的重点。
慈善组织公信力的提高还应积极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为我所用。美国是慈善大国,已经形成了一套健全的慈善评估机制,其中对慈善组织的信用评估就是较为有效的规范。美国专门设立慈善组织评级第三方机构,为超越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评估内容非常丰富,评估之后将结果排名公布,包含正面前10名排名,还包含负面排名,譬如筹款回扣率排名、财务危机排名、劣等机构CEO薪水排名、赠款囤积花不出去排名等。评级结果的好坏直接影响慈善机构将来的筹款能力[9].在巨大的评级重压之下,美国慈善机构不能不提升自己运作的透明度并自觉规范平时行为,以此提高我们的形象。对于这种规范,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已模仿学习。如2010年杭州民政局委托第三方信用评估机构———浙江禾晨信用管理公司,对全市慈善组织进行信用评级,对自愿申报信用评估的公益性社会团体的基本条件、组织建设、人才配备、工作绩效、社会评价等指标进行剖析,将评估等级在AAA级以上(含AAA级)的9个市区级慈善组织在中国社会组织网、《中国社会报》、浙江民间组织信息网、杭州信用管理网等媒体上予以公告。评估等级有效期为三年,在等级有效期内,将对受评单位推行跟踪评估,保证评估的动态性和权威性[10].信用评估能够帮助慈善组织提升透明度,可以督促慈善机构在平时工作中提升效率,勉励慈善组织加大公信力建设。
综上所述,慈善事业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项社会建设[11],在社会转型期,慈善组织只须化重压为动力,通过提升透明度、加大监督、提高从业者素质和实行信用评级等规范,就肯定可以跳出信赖危机,获得公众的信赖和期待,履行好历史赋予的使命。[论文网]